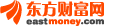宏观点评:30年财税改革启示录:是时候改变了?
回顾一路走来的财税改革( 尤其 1994 年以来),这是一段央地之间财权、事权错配不断加深的历史,也是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收支缺口、不断寻找资金来源(银行贷款、土地收入、隐性债务)的历史,更是中央政府不断化解和规范地方财政和金融风险的历史。 30 年来,财税改革始终在“地方收支缺口变大—新的融资模式兴起—风险积聚—管控化解—新的融资模式兴起……”的循环中往复,而不变的是地方政府日益上升的收支负担。 30 年后的今天,“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或许我们能够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能够出现一些转折。
财税体制改革“五部曲”: 一边做、一边改, 财权上收、事权下沉是主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进程并非完全“一帆风顺”——从央地事权划分的极其不稳定、到中央政府开始放权让利( 地方事权包干制)、再到央地事权逐步明晰(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脉络也逐步明晰。 整体来看,可将财税体制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78 年): 计划经济时期的“摸索”。 新中国成立后,财税体制“百废待兴”。 政府对事权的管理更“相机抉择”, 而央地事权划分的极其不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民经济的震荡。 在经历过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五次上收、 四次下放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迫在眉睫”。
第二阶段( 1979-1993 年): 地方事权包干制“上线”, 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 经历过各项事权的不断上收、下放后,在激发地方经济活力的主旨下, 1978 年起终于将央地事权关系“定音”、 中央政府正式开始放权让利, “分灶吃饭”的地方事权包干制也随之开始建立。
然而事权包干制造成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对于财力尚有余力的地方来说, 财政收入在按包干的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确定的)上缴中央后,剩余的钱都归地方所有。部分地方政府便采用企业税收减免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 并通过企业上缴利润的方式增加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 而对于财力偏弱的地方来说,它们更多是倚靠中央财政进行补贴。 因此,减收增支的中央财政后期难免表现乏力——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也致使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降低,这就催生了财政分税制的出炉。
第三阶段( 1994-2003 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分税制“登上舞台”。 1994 年正式启动了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 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划分了各自财政的支出范围; 再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收入,将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由于很多占财政收入大头的税种均为中央税,因此分税制实施后中央财政开始飞速壮大, 1994 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速高达 203.5%。
与此同时, 央地各自执行的支出任务却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由图 6 可见,在分税制改革启动以后, 央地财政收入的比重发生了逆转,然而央地财政支出却几乎“毫无波澜”。 这也就意味着中央收入增加的同时,其相应的事权并没有随之增加; 反观地方政府,不仅延续了包干制下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责,还“被动”包揽了不少其他事权。 最终央地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情况愈发突出,地方“入不敷出” 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信贷“狂飙”到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 AMC 剥离不良贷款。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并未形成,地方“入不敷出”的结局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干预、 使银行对国企不断提供信贷支持。最后导致了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走高、地方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攀升,中央政府首次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四大行资本充足率。
第四阶段( 2004-2011 年): 分税制的“查缺补漏”。 基于央地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情况,财税体制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为使财政的“阳光”普照城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地方财力以地生财”逐步成为弥合地方财政缺口的另一主路。 在分税制下,土地变现时产生的增值收益无疑成为“香饽饽”,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最便捷的收入来源。 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土地价格剪刀差直接带动了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的升高,同时房地产的快速增长也使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产相关税好转。 随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渐浓,土地出让金从预算外收入调整为预算内收入——从 2007 年起,土地出让收支正式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第五阶段( 2012 年-至今): 现代财政制度的不断探索。 2012 年十八大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主线之一。 2012 年以来虽然不乏探索央地事权和财权之间“平衡点”的案例(譬如 2016 年将多项公共服务职责划分为中央、地方、央地共同承担三类),但一系列“微改革” 其实取得的效果甚微。
金融危机后城投平台的“肆意生长”,是地方政府补缺口的象征。 2008年的“4 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有 75%的资金需要由地方政府提供,原本就运行困难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借款,这也是隐性债务开始累积的“起点”。 而面对地方债务可能违约的“舆情”,政府最后还是通过表内债置换表外债等措施来降低地方金融风险。 自 2015年以来,我国已开展了四轮隐性债务置换工作,其中前两轮是以置换债的形式,后两轮是以特殊再融资债的形式。
目前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依旧很重,尤其在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不断下滑、 偿债压力却有增不减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似乎在承担着“不能承受之重”。 与此同时, 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路径也并非“一帆风顺”,资金传导过程中也时有资金分配不规范、资金未及时下达等问题发生,这无疑使地方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能会如何推进? 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预计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一方面, 事权可适当上收, 将国防、国家安全等重大事务集中于中央,这样也可以减少委托事务、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适当提高央地共享税中地方的分成比例、或将部分中央税转变为央地共享税,以此提高地方财政的“造血”能力。 比如可以提高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均为央地共享税)中地方的分成比例,以此调动地方支持企业发展的主动性;还可以将原本属于中央税的消费税纳入央地共享税,这样还能减少市场中变相逃税、漏税的现象。 同时,在会计审计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逐步将资金直达机制常态化,使中央转移支付机制可以更快下达、更精准投放。
财税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 一是决定了中央和地方“谁主沉浮”。 在地方事权包干制时期, 中央政府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结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突出,地方财政居于中央财政之上。但随着分税制的“横空出世”,中央财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二是决定了中央和地方谁加杠杆更明显。 在包干制时, 中央和地方加杠杆的力度“难分伯仲”,不过分税制后,收支更可观的中央承担了一段时间的加杠杆任务。而后随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的逐步加大,地方又逐步取代中央、成为加杠杆的“主力军”。但出于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地方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等原因,地方加杠杆似乎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是决定了基建投资将如何前行。 包干制时期大幅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期间基建投资增速涨势也十分喜人。进入分税制后,一开始基建增速有了比较明显的放缓。而后伴随着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地方政府加杠杆力度的提升,基建又步入到“加速期”。但着眼当下,地方政府加杠杆已处于一个“瓶颈期”, 及时为地方财政“充电”显得至关重要。
风险提示: 财税体制改革进度不及预期; 政策定力超预期;出口超预期萎缩;信贷投放量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