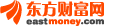美国“再工业化”系列研究(一):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何以艰难?
美国“再工业化”启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开启“再工业化”战略,以2009年《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以及2010年《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标志。奥巴马启动“再工业化”的经济考量,包括经济复苏、经济结构优化与国际收支平衡。2017年以后,特朗普延续了“再工业化”愿景,但手段与奥巴马时期明显不同。特朗普启动“再工业化2.0”的经济背景是,美国经济结构并未改善,且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比较来看,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政策目的均是重新发展制造业,且都支持加大基建投资。比较来看,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政策目的均是重新发展美国制造业,且都支持加大基建投资。但不同点在于,1)政策思路上,奥巴马侧重“重建”,特朗普侧重“回流”;2)扶植企业方式上,奥巴马更依赖于政府支出与补贴,特朗普主张减税并增设贸易壁垒。3)细分领域上,奥巴马倾向于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前瞻性地布局中长期制造业竞争;特朗普更重视传统化石能源、国防等发展。
美国“再工业化”成效评估。总的来看,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战略并未获得积极评价。2010-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滑,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下滑,商品贸易逆差没有明显改善,说明政策未能阻止19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大趋势。不过,全盘否定“再工业化”的成效或也不够客观。虽然美国制造业本身的增长表现平淡,但美国私人投资的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尤其基建投资明显增长,制造业领域的FDI加快流入,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人才教育与就业加快发展。
美国“再工业化”何以艰难?1)商品内需有限。次贷危机后,美国商品消费占比继续维持下降趋势,其中耐用品消费占比下滑更明显。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商品消费增长的瓶颈,限制了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增长的空间。制造业需求下滑,有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顺应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2)国际竞争加剧。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等“初级成本”在全球比较中处于相对劣势。中国制造业综合实力的上升,无疑加大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难度。此外,以苹果公司的外包战略为例,美国产业政策可能不足以扭转“行业领袖”已经铺垫好的全球化之路。3)产业政策断崖。奥巴马时期的政府支出未能延续高水平,政党轮替破坏了产业政策的连贯性,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对于制造业发展可能弊大于利。4)金融发展过度。美国金融业繁荣可能侵蚀制造业发展空间。由于金融业薪酬较高,制造业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自然处于劣势。金融市场繁荣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短视化。美国上市企业倾向于将利润更多用于股票回购与分红,而不是增加资本开支,导致长期投资不足。5)美元指数升值。次贷危机后,美元汇率呈现走强趋势,对美国制造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