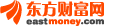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利率(下):1998-2019:RECALIBRATE
自1990年代中期起,美联储开始了新一轮的决策框架“再校准”,主要表现为对汇率和国际收支失衡关注度的大幅下降,以及对美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关注度的大幅提升。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广泛冲击,美联储探索到了非传统货币宽松的脆弱边缘,此后在正常化传导机制重建的漫漫长路上艰难努力。
LTCM危机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注度的提升(1998-2000):高杠杆交易的对冲基金拉开了美联储主动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时代的序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没有对美国经济形成实质性冲击,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以极高杠杆投资于俄罗斯国债而破产,美联储为应对金融风险潜在传导的经济下行压力而提前实施降息,并组织大型商业银行对其进行救助(Bail out),国内金融风险重要性上升。
全球化加速背景下,货币宽松纵容房地产泡沫(2001-2006):进入21世纪,直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进入一个“呼风唤雨”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极为高效的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令美国经济维持相对较高增速的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高通胀的潜在束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2000-2001年的短暂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之后开始采取二十年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宽松操作,但在泰勒规则的加持下,理论上潜在增速的上行掩盖了经济结构日渐向房地产领域倾斜的泡沫化风险,美联储在“高效的逆周期调节”的表面繁荣下选择性地容忍了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相结合的巨大金融泡沫的形成。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非传统货币宽松扭曲传导(2007-2013):全球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打破了美国货币政策能够长期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神话。2004-2006年的急速加息除了再一次证明全球化背景下美联储的通胀担忧是过度的之外,还充分暴露出房地产泡沫化阶段美国金融体系通过“影子银行”交易高杠杆过度持有MBS等“有毒资产”,导致本就相当缺乏的资本金在危机期间受到大量侵蚀,银行业流动性危机向实体经济融资层面蔓延,各部门都陷入普遍性的向内坍缩恐慌。美联储迅速降息至零利率下限,但刺激复苏作用微弱;2008年间创设了一系列融资便利工具,向金融市场提供巨额流动性,但未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最终选择启动四轮大规模长期国债和MBS购买计划,进入非传统宽松政策的无人区。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流动性枯竭蔓延的极端情形下,美联储的操作是果断且必要的,但由此导致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损伤和传导效率的大幅降低代价也是巨大的。
“大缓和”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艰难重建(2014-2019):银行体系流动性泛滥、缺乏技术进步突破、全球化进一步走向深入,共同导致美国长期增长趋势与货币政策之间逐步脱钩,进入“大缓和”时期。美联储于2014年9月宣布了“货币政策正常化原则与计划”,首先构造了基于IOER的新利率走廊以实现有效的加息,此后自2017年9月开始持续约两年半的“缩表”操作逐步减少了金融体系过剩的流动性,部分恢复了短期利率与实体经济资金供需的连接,通过推升长期实际利率、小幅压降长期通胀预期的方式对长端利率形成总体抬升作用,但无法改变美国长期国债利率领先性下降、滞后性提升、与美国货币政策关联度降低的特征。直至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QE所导致的货币传导效率损伤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风险提示:美国核心通胀高位黏性较大、导致美联储货币紧缩超预期风险。